
公正 严谨 真实 客观

公正 严谨 真实 客观

图片来自网络
可能有些年龄大了,我已经很久不看电影了。最初是不再到电影院看电影,后来是不在电视、电脑上看电影。当然,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,我也不想去深究它了。可是,我记得,我曾经是那么热爱看电影,甚至为了看电影,不惜奔波十几里路,而且是乐此不疲。那应该是我的童年、少年时代了。
那时候,电影放映队一进村,乡村就骚动起来。大大小小的孩子不停的去大队探看电影放映员的举动,如果能亲耳听到放映员说说电影的名字,那就有了新闻发布的素材,如果再能摸摸放映机,看看装电影片子的盒子,就更有的吹牛了。其实,这都不是最主要的:要放的电影,邻村刚放完,一般不会换片子;至于那些机器什么的,都摸了多少次了,再摸一次,只是刷新数量而已。孩子们最关心的,还是放电影的场地在哪儿。我们村大,可以放电影的地方也多,有时是在中校旁边的小树林里,有时是在后校的院子里——那曾经是一座很大的庙,有时就在村子中间的水塘边上,有一次却是在沂河的河滩上……孩子们一旦知道了准信,就会一哄而散:预地方去!
只一袋烟的工夫,看电影的黄金地段就被十几二十个长方形、正方形瓜分完毕。其间,当然会有领土纠纷,会有外交风波,最终总能折冲樽俎,皆大欢喜。如果谈判解决不了问题,也要诉诸力量,比如谁个子大,谁拳头硬,谁家离这里近,等等不一,冲突双方总能掂清斤两,做出或攫取或妥协的决断。若干年之后,当我开始关心国际新闻时,我感觉那些国家间的把戏,我们小时候就玩过,不由哑然失笑。
我那时个子小,胆子也小,自然不在占地方的孩子之列。但是我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坐,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同学,他经常会占有大片的地方,而且他还要常常抄我的作业,我大致能从他那儿得到安两三个座位的地儿。我开始不明白他们为啥要占有那么多的地儿,他们一家子顶多安放四五条板凳而已。后来,我看到我找他要地儿时,他脸上的优越的表情,不复是要抄我作业时的嬉皮笑脸,那么像彼时我的表情,我忽然理解了他:人人都需要尊重啊!我想,他也许特希望村里天天放电影吧,那样他就能天天得到人的尊重了。我那时就有此感触,可见很小就有了推己及人的悲悯情怀。
上黑影时,电影场上就慢慢坐满了人,等着大队干部陪着放映员吃饭。大家并不焦急,大人们三五成群地在拉家常,孩子们围着场子疯跑,好像都忘了是来看电影的。人群外围也偶尔有几个小贩,但是他们好像游离于人群之外,很少有人问津。偶尔有一个妇女拗不过孩子的纠缠,或者有一个半大小子想充英雄,过来买一包瓜子或者几块糖块,立即就成为全场的焦点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买东西的人立即觉得自己矮了半截,默默丢丢地买完东西,做贼似的快速离去,简直是弃小贩如敝屣,避小贩如猛虎。那时的村风朴素而纯洁啊。
当放映员打着饱嗝,喷着酒气,蹒跚而来时,人们依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,因为他们知道大队书记还要讲话。书记乘着酒兴,主要词汇就是“啊、哎、嗯、是不是”,他自己也许不知讲了什么,社员们也不关心他讲了什么,他们只觉得这样才像领导,领导讲话那就是像太阳落了天就黑一样的自然而然。书记过足了瘾,终于放下话筒,电影才正式开始。电影场并没有安静下来,除了来晚的人在呼儿唤女,昨天刚在邻村看完电影的已经开始义务剧透。场上安静下来,得是电影快进入高潮之时。
此时放眼看去,电影场黑压压地都是人,黄金地段坐满了人,预了那么多地儿的把人情都送完了,他们到头来也只是占有一个板凳空儿。黄金地段外围也坐满了人,他们大多是成年人,经历多了,什么都看得淡了,却又尚未返老还童,对电影可看可不看,只是在家也无聊,最终还是搬着凳子来了。再外围,就是外村来看电影的人了,他们大多站着,只有极个别的,坐在支起的自行车上。还有一些人,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,他们来晚了,就站在电影幕布的后头,看翻影,如果没有字幕出现,倒也差强人意。他们能随遇而安,却也还不是隐士,隐士此刻应该高卧梦周公了。
电影常常放到一半,发电的汽油机就会怠工,放映员就要来回折腾发电机,折腾上半个小时,发电机休息够了,就会满血复活,电影重新放映。折腾不好,一些年龄大的人就会陆陆续续搬着凳子离开,最终失去耐心的放映员只得宣布明天继续放映,孩子们才会满意地离去:明天还有电影看!
孩子们不仅本村的电影要看,邻村的电影也绝不放过。一旦得了准信,,吃过晚饭,孩子们就会呼朋引伴,呼啸而去。那时家家孩子多,并不金贵,基本就是放养。孩子们在家里也是打打闹闹,不在眼前反倒清静。小青年们也喜欢出村看电影,其意却常在电影之外。那时青年婚配农村大多还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小青年们偷偷摸摸、甜甜蜜蜜一阵子,修成正果者却也寥寥,只留下一段青涩的回忆。偶尔有修成正果的,双方父母也还是要麻烦媒人,否则会被众人视为异类。只是白便宜了媒人,不跑腿不动嘴倒落下一场酒喝。
我们家那时管得稍微严点,路远的地方,大概超出十里路就偶尔会禁止去了,邻近几个村子倒也并不禁止。可是有一回着实把我父母吓坏了。那次是木作村放电影,离我们村才三四里路,我不但自己去了,还把小我两岁的弟弟也带去了。我们去得早了点,在等待放电影的时候,到处乱转,被大姨遇上了。其时大姨一直没有孩子,见了我们,金贵得不得了,就把我们拉过去,和大姨夫一人搂着一个看电影。看完电影,大姨还没稀罕够,干脆就把我们弟俩领回了家,与大姨夫一人搂着一个睡了。我们那时一方面浑浑噩噩,一方面又受宠若惊,没了脑魂;大姨大姨夫也许被意外的喜悦冲昏了头,也许是临时起意,竟然没有谁想到我们父母的感受,也没叫我们同村的孩子捎个话回去。第二天,我们一觉醒来,大姨才笑嘻嘻地告诉我们,你们爸爸妈妈昨晚兴师问罪来了,说回去还要揍你们哪。我们也着实吓得不轻,可是大姨很快端上萝卜卷,稀饭里还撒了一层麻花,我们就把害怕忘了。吃完早饭,大姨让我们一人扛了一个冬瓜回去了。回到家,母亲也并没有揍我们,而是忙着削冬瓜,拌臭豆子去了。大姨做的稀饭可真好喝,可惜前几年,大姨已经不在了。
看电影固然快乐,来去的路上也别有风味。去时,孩子们你追我赶,带着希望,撒着欢儿,尥着蹶子,活像一群精力充沛的儿马。来时,大家或者议论纷纷,或者静思回味,野外的虫子叫声此起彼伏,不知不觉就回到家里,夜路不经走呢!记得上了初中之后,附近的麻湖村放电影,我们几个同学等老师查完岗,偷偷溜出去看电影。其间,要经过武河大桥,桥上雾气弥漫,河里的水腥气一波一波地泛上来,却又让人感到了夜的神秘!今天想来,那晚的水雾至今还是那么朦胧而鲜明。
后来,到城里上学,然后工作,看电影就基本在影院了。影院有影院的方便,却没有了看电影之外的趣味,是更单纯了呢,还是更单调了呢?

作者简介:乔俊文,郯城县美澳学校语文高级教师,临沂市作协会员,1969年出生于黄山镇安头村。喝沂河水长大,农村的人生百态、社会变迁,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无意识之中,和乡村的血肉相连,与乡亲的呼吸与共,对故乡的魂牵梦绕,汇聚成了他笔下的依依乡情。

采稿:孔明百科网 编辑:张新杰 杨俊飞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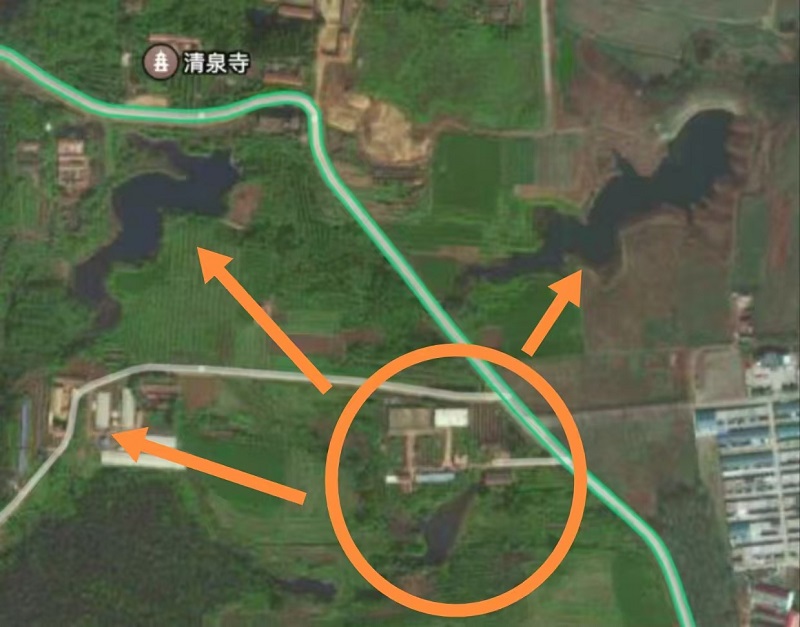


Copyright © 2020-2026 智圣千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鲁ICP备2020036221号-1